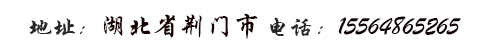探其上下,究其左右清末大学者俞樾谈
|
本人酷好诗词和楹联,偶然接触到俞樾(yuè)的作品,一读就爱上了。爱屋及乌,仔细研究了俞樾,觉得他是一个或多或少被忽略的奇人。 用“学者”二字来冠名俞樾,似乎小视了他在国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可以给他戴上的头衔太多了,都是大师级别的。他在经学、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楹联、书法等领域,都是现象级存在。他修书五百余卷,著作超身。其后半生在苏浙一带的官办和民办书院讲课,相当于现在的“院士”,章太炎、吴昌硕、戴望、崔适等都是他的门徒,这些学生哪个人拎起来都是一本书。清末有一句话流于坊间,“当朝宰相李鸿章,山中宰相俞樾,”将两者并提,说的就是他文学巨匠的地位。他中过进士,当过官,前后七年有过两个官衔:翰林院修撰,河南学政,可不久被罢官了。纵观他的人生之路,虽有坎坷,也非大起大落。 瞭望其一生,重中有三:一是大儒家庭背景,上下七代不以官显,却因文著。二是国学通才,涉猎百家,高山仰止。三是对中医的“废医存药”说,这个虽有争议,在当时是一种冲破藩篱之举。 家族溯源 俞樾出生在浙江省德清县,家族本是务农。成为当地望族是从他爷爷俞廷镳(biāo)开始的。俞廷镳是俞家第一代有记载的文人,他虽学识渊博,一直考举人不中。到七十岁考分才达到了要求,浙江巡抚见他年事已高,和他商量可由皇帝恩赏举人:“七十岁让与他人,由皇上恩赐”,不占名额。俞廷镳欣然应允。当发榜时,他却只落副榜。对他来说,可以理解为只是给了一个荣誉。对此,他本人倒很坦然:“吾已年老,以此留与子孙,不亦善乎?”。无论如何,也算开了俞家先河。这一年是乾隆五十九年(年)。 俞廷镳寿至七二,五十六岁时喜得独子俞鸿渐。他和孙子俞樾没有交集,因为等到有了俞樾,他已去世二十多年。可就是这个爷爷,不仅奠定了家族兴旺的基业,著书治学上也有所成。为了纪念,俞樾自费出版了爷爷的遗稿《四书评本》,并请李鸿章题了书名。 话说到了俞樾的父亲俞鸿渐,就稍有点名气了。他考上了举人,应该是家族第一人。虽然十一次会试不中,毕竟也当了个中不溜的官——湖南巡抚的幕僚。后来俞鸿渐辞官开家馆(私塾)当老师,并著书立说,有十几卷著作留世,称得上建树颇丰。 俞鸿渐有两个儿子,长子俞林,幼子即俞樾。兄弟二人小时候一起随母亲姚太夫人(和岳飞他妈一个称呼)多地求学,乡试先后考中举人。哥俩数次一同赴京会试,哥哥终未考取(也有说中副榜,未详考),弟弟在道光三十年中进士。科举制度是进阶式,分秀才、举人、进士、殿试四级。古人有“穷秀才,富举人”的谚语,举人作为候补国家干部是有机会转正的。进士就不用说了,起步就是县级干部,正七品。 举人哥哥不久就被分配到福建当官,进士弟弟呢? 与曾国藩、李鸿章的交情 先来看一下俞樾的生卒日期:年12月25日—年2月5日。他活了八十六岁,靠死了清朝的三位皇帝,道光、咸丰、同治,差一年就靠死光绪和慈禧太后,在那个时代算是顶级长寿。他一生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义和团拳民等,时局前所未有之纷乱繁复。他的出生在道光元年。道光皇帝在位三十年,就在道光三十年,(年)俞樾考中进士第十九名。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年的主考官是曾国藩,在保和殿复试阶段的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依题作诗。俞樾的诗首句即不凡,曰:“花落春仍在”,曾国藩阅后大喜,赞道:“他日所至,未可量也。”因俞樾的诗文被老曾看中,遂将其名次移列复试第一。 保和殿俞樾答题的全诗如下: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淡浓烟尽活,疏密雨俱两。鹤避何嫌缓,鸠呼未觉忙。峰鬟添隐约,水面总文章。玉气浮时暖,珠痕滴处凉。白描烦画工,红瘦助吟肠。深护蔷薇架,斜侵薜荔墙。此中涵帝泽,岂仅赋山庄。 这首诗是五言排律,对仗极为工整。我个人看来,一处韵有误,一处平仄有误,可能和他的南方口音有关,但小误不失大雅。即席写出如此之作,搁现代只有佩服的份儿。难能可贵的是,此诗一反题目伤春的内涵,巧妙地利用“花落春仍在”切题,立意转而积极向上,犹如对江河日下的大清打了一针鸡血,故深得曾国藩好评。 该诗确立了俞樾的基调,他一生的著作以《春在堂全书》命名,他在苏州的家“曲园”正堂的匾额“春在堂”由曾国藩赐墨,都出自此。 就这样,俞樾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官员生涯,咸丰元年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是个候补官员,只不过是有潜质的进士在皇帝身边等待机会。哥哥俞林一起进京赶考,但是落榜了,虽然未考上进士,留在京城机会也会多一点,就和弟弟一起搬进棉花胡同居住。果不其然,俞林谋得一个实录馆誊录的职位,这是一个临时机构,解散时得到了外放福建做官的机会,最后官至福建福宁州知府。 在此前后,曾国藩引荐俞樾和咸丰帝交谈了一次,咸丰帝赞叹他学识渊博。受到青睐的俞樾在咸丰二年()被授编修。翰林院编修不过正七品文官,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母亲也从老家来和兄弟俩团聚,春风得意的俞樾便从棉花胡同举家迁北京南柳巷。我去过南柳巷探访,未寻见俞樾在此地的蛛丝马迹,而后来住在南柳巷的林海音却成了招牌。 清末名臣曾国藩是第一个和俞樾有交集的重臣。因为当时主考官与考生有名分上的师生关系。每一次考中的学子,都要拜当次的主考官为师。曾国藩的学生非常多,大清一半以上的文臣武将官员,都叫他老师。俞樾也不例外,拜其为业师。曾国藩惜才,俞樾尊师,二人私交非常好,经常借道为访,诗书往来。 俞樾一生写下很多诗词楹联,其中写给曾国藩的非常多,有“溜须拍马的,”比如这一首: 《题曾文正公手书一侧后》 淋漓妙墨一编开,作对还如笑语陪。 我读公诗拜公像,昨宵公自梦中来。 有祝寿的: 《贺曾国藩六十寿联》 大勇在安民,运际中兴出名世; 小春欣遇闰,天教两度祝延龄。 曾国藩谢世后,他写了几幅的挽联,其一: 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 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 曾国藩在评价最得意的两个弟子时说过:“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对俞樾潜心研学给予高度褒扬。 至于李鸿章,这又是和俞樾关系非凡的清朝重臣。李鸿章比俞樾小一岁,先于俞樾考上进士,二位在翰林院有过共事,又都是曾国藩门下的饱学之士,难免惺惺相惜,互为欣赏。他俩还有一层关系——同科,就是同一年(甲辰恩科同年)考上的举人。这一层关系在当时非常重要,政治小团体、朋党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一层关系使得他俩有密切联系,后来发展成挚友,就不详细说了。李鸿章一直为官,权倾朝野。他和俞樾的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寿终正寝。他也没能耗过俞老爷子,早其六年殁。李鸿章曾经任两江总督,任上多有照顾被罢官无职无钱的俞樾。下文俞樾从天津南还苏州的第一份工作——苏州紫阳书院的教席就是李鸿章介绍的。还有他大儿子俞绍莱的官职,二儿子俞祖仁的候补官职,都是李鸿章安排的,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看一下俞樾写给李鸿章的寿联和挽联,感受一下他的文采: 《贺李鸿章五十寿联》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为相公寿; 治内用文,治外用武,长城万里,殿天子邦。 《贺李鸿章七十寿联》 五百年名世之才,上纬天维、下理地轴; 七十载从心所欲,西摩月镜、东弄日珠。 《俞樾挽李鸿章联》 一个臣系天下重轻,使当年长镇日畿,定可潜消庚子变; 八旬翁完真灵位业,溯壮岁同游月府,不能再逮甲辰科。 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事到如此,俞樾理应顺风顺水,官途无量。恰恰这个时候,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看人生的结局就知道了。 咸丰五年,在翰林院任编修的俞樾通过了差放考试被任命河南学政。 先解释一下名词“差放”,它是考差和外放的合称。考差是科举制度在清朝形成的一种独有制度,是对派往各省去的学政、乡试主、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学政任期三年,主、副考官任期一年。考差资格是有门槛的,条件是进士出身的京官。先是从翰林院找人,后来扩大到六部。还有一条,参不参加考试自愿。“外放”指京官到地方任职。差放考试虽然是自愿,但是京官趋之若鹜,尤其是在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待业”的进士们。 “差放”有三个好处,一是相当于现在到基层代职锻炼,回头大概率重用;二是能考上的人都被认为是得到了一个最高级职称,可以认为是“院士”。三是经济上会得到质的飞跃,朝廷会给予路费、安家费,俸禄会大大提高。有一本书《春明梦录》中说:“从前京官,以翰林最为清苦,……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份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还有副主考,年金也不少。这和七品翰林的年工资为九十两白银加四十五斛大米形成巨大反差。 “学政”是个什么官?不就一个地方主考官吗?其实不限于此,有点主管文化教育和人事的副省长的意思。这个副省长是比喻,因为它不设品级,京官下放,任期三年,属于皇帝的钦差。学政不用看别人脸色行事。历史上著名的学政有:湖北、四川两任学政张之洞、福建学政纪晓岚。 上面说了,学政是地方主考官,肩负人事部门职责,之所以朝廷通过“考差”派人,就是要防范作弊。学政管“岁、科”两试,属于州一级考秀才的,是科举的初级考试,有出题的权力。俞樾动了脑筋,他在出题上大胆革新,防止死记硬背和押题,想以此考出考生的真实水平,发现人才。科考的题目大多从四书五经里面挑一句,俞樾不按常理出牌,他把句子掐头去尾,重新排列组合,拼凑一个新的题目。这在当时被称为“割裂题”,没点真才实学真做不出来,有点墨水的也难以下笔,所以引来考生怨声一片,纷纷上访告状。有曾国藩罩着的俞樾本不怕这些,可偏偏他出的题目让别有用心的人找到了漏洞。比如题目“君夫人阳货欲”说成是指的皇后要出墙;“王速另出反”则是鼓动宗室成员造反。很多题目都附会出反义。 事情闹到“纪检委书记”御史曹登庸那里,曹登庸便以试题“割裂经义”上奏弹劾俞樾。咸丰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如不是看在曾国藩的面子,俞樾可能小命就没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俞樾被罢职,永不叙用。 是年三十七岁,仕途就此结束,祸福未可知也。 八年的颠沛流离 清咸丰八年(年)俞樾三十八岁。罢官后在开封过完年,春天也到了,便携眷南归。 太平天国运动闹得正欢,南归的道路险且阻,绕着圈子抵达苏州后,在饮马桥赁石琢堂的独学庐而居。侨寓苏州之始。 这年夏天开始治经写书,学习篆隶书法。打造新生活模式。 到了秋天,在江苏巡抚赵德辙的推荐之下主讲苏州云间书院。这是他讲学的第一个书院,可以赚些钱养家。 好景不长,咸丰十年(年)太平军攻打苏州,俞樾一家开启了避乱之旅,先后在新市、绍兴、上虞、宁波、定海、上海漂泊了两年。此间居无定所,无甚好讲。可以提一嘴的是全家老小积蓄将尽,在上海黄浦江租一个小船度过同治元年的春节,随后乘船直奔天津。 用贫困交加形容当时的俞樾不为过。但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亏他不是等闲之辈。同治元年(),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早已被镇压下去,相对平和安全。他的朋友潘霨提升为天津府知府,是天津的一把手。再加上北洋大臣的前身“三口通商大臣”设在天津,时任的崇厚侍郎的弟弟崇实和他是同科进士,有这一层裙带关系,去天津投靠他们是个好主意。到了天津,并未如他想象那般美好,毕竟寄人篱下。给个文案小差事干干不够养家糊口,常常靠借贷生活。好在俞樾不止那么两个朋友,口碑又好,所以渐渐安顿下来。在天津一住三年。崇厚推荐他修《天津府志》,有些报酬。有了时间可支配的俞樾著作大丰收,写了六十三卷书。此间,他还嫁了一个女儿,为两个儿子办理了婚事。 天津是他生命中短暂又闪亮的一驿,在离开前,富商张汝霖资助他出书,《考工记世室重屋明堂考》同治四年()春天刻成,得到恩师曾国藩的好评。对张汝霖帮助刻书一事,俞樾念念不忘,并言“余书行世,实始于此”。他的意思是这是他第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书。 同年秋,俞樾举家再次南还苏州。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ongxinge.com/zxls/12052.html
- 上一篇文章: 推动5G消息在金融业商用银联数据四川移
- 下一篇文章: 排列出中国历史上抵抗异族的十大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