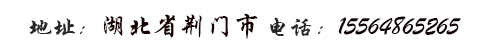达拉特历史文化综述
|
达拉特历史文化综述 曲辰/文 达拉特有一部蕴集深沉的历史。在振兴达拉特旗的新的历史时期,发掘和总结达拉特的历史文化,让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实现有效对接和有机结合,把历史文化融入现代文明,无疑是必要和有意义的。达拉特悠久丰富的历史内涵,深厚绵长的文化积累,独具特色的人文造化,应该激励达拉特人世世代代奋发进取,锐意创新。 历史的悠久性 在远古的地质年代,达拉特曾经发生过山崩地裂的动荡,有过沧海桑田轮回的水陆变迁;从水深火热中走出来的古代先民,经历了炼狱之苦,创造了远古文明;早在战国时代,达拉特便有了初具规模的拓荒耕耘;作为多民族活动的舞台,许多北方少数民族都曾经在此秣马厉兵、生活繁衍;达拉特是河套地区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共兴的摇篮;达拉特曾经藏龙卧虎,孕育过兵强马壮、威镇北方的匈奴;蒙古族雄踞虎镇,长期守护建设,功勋卓著;赵武灵王铁骑奔突,秦皇汉武调兵遣将,历代战事累累;司马迁造访,汉武帝巡视,王昭君出塞,更是千古佳话。 公元前两千多年以前,夏、商、周时期,生活在达拉特的游牧部落,见于记载的有土方、鬼方和猃狁等。这些游牧部落与中原奴隶主国家有过许多战争。《诗经·出车篇》中“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的诗句,即是关于周伐猃狁的记载,说的是公元前八世纪周宣王曾派大将南仲筑朔方城并北伐。朔方城是统管现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首府,城址位于今杭锦旗独贵特拉乡境内(独贵特拉历史上属达旗)。商周时的狄,春秋战国时的林胡、楼烦,秦汉时的匈奴、乌桓,魏晋南北朝时的鲜卑、敕勒、羯、氐、羌,隋唐时的突厥,辽时的党项、契丹、吐谷浑,元明以后的蒙古族,都在此驻牧。几乎所有北方草原民族,都曾把达拉特作为生存发展的基地。 达拉特民间至今流传着一句俗话,“走胡地,随胡礼”。劝导人们入乡随俗,为什么用这么一种说法?什么是“胡地”?什么是“胡礼”?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这一方土地为胡人所踞,是为“胡地”,“胡礼”即胡地的规矩礼仪。战国时期燕赵等国迅速强大,不断以武力兼并周围游牧民族,赵国在赵武灵王即位后“北破林胡、楼烦”(《史记·匈奴列传》),继而改革军事装备,于公元前年下令军队一律去掉不适宜作战的华夏衣裳,改穿胡人的轻便服装;并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技术,用行动敏捷的骑兵代替笨重的战车,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故事。我们这一方水土曾经使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眼界顿开而大有作为,导引了华夏大地的服装改革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也确曾是达拉特所拥有的历史文明。赵武灵王占领了河套地区以后,在今天包头郊区麻池建立了九原郡,管辖大青山以南包括达旗北部的地区。包头郊区现更名为九原区,便据此而来。赵武灵王为了把九原作为南下进攻秦国的军基地,从京城邯郸迁来大批移民,开垦黄河两岸的土地,达拉特的农耕开发即源于此。达旗昭君坟乡现存的二狗湾古城遗址内曾出土布币和刀币,证明该城是武灵王时所筑,是九原郡属下的城池。秦始皇修通直通道以后,派大将蒙恬越过黄河,沿路筑了许多城堡,昭君坟乡境内的城拐古城遗址即蒙恬所建城堡。 公元前年,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后,巡辽西,历北边,至九原,而后沿“秦直道”回长安。历史学家司马迁随汉武帝同行,由北而南穿越达拉特之地,《史记》中关于鄂尔多斯地区风情的记载,即系此行沿途所见。 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和亲,又沿“秦直道”由南而北经达拉特至匈奴大本营光禄塞。因达拉特沿河地区水草丰美,又距光禄塞较近,王昭君曾经在达旗沿河地区传耕教织,播扬过中原文化。 秦始皇时期曾移民戍边,达旗境内曾又一次出现农耕经济。整个秦、汉时代,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时好时坏,战争连绵不断,由于“秦直道”在达旗境内贯通的缘故,汉匈战争中达旗属于两家必争之地,仅东汉时期匈奴大规模叛乱11次,有两次平叛战争即发生在达旗境内。 宋代辽伐西夏的大规模战争,发生在达旗境内。成吉思汗发动统一战争以后,蒙古族开始进入达拉特,西夏投降蒙古后,达拉特之地即属蒙古族领地。整个元帝国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尽系元朝马苑,达拉特属于哪一个千户马苑难以考证清楚,但属于中书省大同路管辖史有明载。明洪武三年(公元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征讨鄂尔多斯地区,元朝守将扩廓铁木耳败逃,明朝将蒙古族八万降户原地安置,设军事卫所管制,五花城千户所即设达旗境内。十五世纪中叶,蒙古族军事势力再次进入鄂尔多斯,明朝曾派大军“搜套”“剿套”均未能奏效,不得以于成化九年动用四万军役沿鄂尔多斯南部修筑边墙千七百里,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名义上是防御蒙古族南侵,实际是把河套让给了蒙古族,为之《明史》有“弃套”之说。这道城墙在鄂尔多斯南部尚有遗迹,人称“明长城”。蒙古人从漠北大规模南下时,守护成吉思汗陵的鄂尔多斯部也于明成化年间进入达拉特,将“八白室”置放于王爱召,世代守护。明、蒙和好时期,蒙古族引进藏传佛教,并在达旗树林召东南四十里处建起规模宏大的召庙,(俗称王爱召),明朝还赐名“广慧寺”。清朝统治中国后,对鄂尔多斯蒙古族上层给予优惠政策,让鄂尔多斯蒙古族处于半自治状态,同时又用盟旗制度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伊克昭盟各旗扎萨克的“会盟”之地便设在达旗王爱召。清顺治六年(公元年)设立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达拉特旗)时,由成吉思汗二十一世孙沙克扎即扎萨克位,达旗最后一任扎萨克康达多尔济是成吉思汗三十五世孙。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巡幸鄂尔多斯地区,两次进入达旗境内狩猎。 文化的典型性 在漫长的历史上,赵武灵王对达拉特有过开发之功,北方地区许多草原民族都曾经在达拉特生存驻牧,秦始皇修路筑城使达拉特的闭塞状况有所改善,屯兵垦荒使农耕经济在赵武灵王的农业开发之后再一次萌芽。然而,纵观达旗历史,建置归属变动频繁,占据争夺交替不息,草原民族流动往来,中原文化以及早期草原民族的文化,因变动和流动等原因而遗存甚少。达拉特从十三世纪中叶蒙古族入居起,元帝国之后虽经明、清两代动荡,蒙古族再没有离开,一直是达旗的主体民族,达拉特的历史文化是以蒙古族文化为核心而形成的。蒙古族文化博大丰富包罗万象,又由于清朝统治者对鄂尔多斯蒙古族实行划地为牢的封闭政策,客观上使蒙古族文化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与传承。但是,达拉特的历史文化又不是单纯的蒙古族文化。十六世纪中期,蒙古族领主俺答引进了黄帽派喇嘛教,喇嘛教紧紧依附蒙古汗权扩散发展,从而使藏传佛教文化得以长期传播,成为蒙古族群众的普遍信仰。蒙古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例如蒙古族最神圣的祭成陵仪式中,加进了喇嘛念经作法的程序。今天居住在达旗王爱召遗址处的达尔扈特后裔以及达旗境内的蒙古人,门前祭台上高竖的象征成吉思汗军威的“苏鲁锭”,样式已不像蒙古式长矛而有点像藏式三叉戟,便是藏传佛教文化与蒙古族传统文化交融的痕迹。今日之所谓“蒙医”,实际是从理论到临床对藏医的全盘移植。尽管藏传佛教文化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但其影响极大,渗透甚深,蒙古族民间至今保留着农历十月二十五日“点灯灯”的习俗,就是纪念黄帽派喇嘛教创始人宗喀巴的生日。藏传佛教经过长期传播以后,和蒙古族文化紧密结合,成为蒙古人的普遍信仰。清朝于康熙三十六年(年)颁布了“借地养民”的政令,允许蒙古王公与内地汉人合伙种地,这条开放性政策颁布以后,晋、陕地区贫苦农民大量进入河套地区,即历史上的“走西口”。西口之路有两条,主要的一条从陕西省府谷县古城入蒙,经准格尔旗纳林镇进入达旗马场壕——新民堡——王爱召——树林召——大树湾,而后至包头。西口之路南北穿越达旗,西口之路上的许多逃荒者在达旗逐渐定居,今天生活在达旗的汉族人的祖先,绝大部分都来自晋、陕地区。西口之路的开通,首先使达旗的土地开发逐年扩大,农耕经济逐步发展,从而也掀开了蒙汉人民共同开发建设的历史。伴随着纯牧业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的变革,汉族的农耕文化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又开始互相交融。蒙古人腊月二十三祭灶,便是蒙、汉文化融合的结果。蒙古人祭灶由祭火演化而来,源于原始的火崇拜,传统的祭祀方式是将牲畜骨头煨于火上。晋、陕汉人很早便有祭灶习俗,并且相传玉皇大帝腊月二十三派灶神下界巡视,于是在这天祭灶。蒙古人将祭火改为祭灶并且将祭祀时间也确定为腊月二十三,是受汉文化影响而演变的。当然,由祭火改为祭灶,也反映出蒙古族从游牧到定居的生活方式改变。西口之路对于达拉特旗来说,是一条闪耀着历史文明的道路,蒙汉人民走出封闭、携手共创,民族文化相得益彰、融合升华,均源于西口之路的开通。从清初康熙年间至清末贻谷放垦,晋、陕地区汉人通过西口之路大量入蒙,蒙汉人民在生产、生活上逐渐结为共同体,蒙汉文化的融合交流也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这种以蒙汉人民共同生产、生活为基础的文化融合,从层面上和范围上均前所未有,并且展示出强大的发展生命力。达拉特盛传不衰的漫瀚调民歌,即是蒙汉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流行在达拉特旗的《二道圪梁》、《打鱼划划渡口船》等漫瀚调民歌,以蒙古人的“坐唱”和汉人的“打坐腔”为媒介,融蒙古族短调民歌和汉族爬山调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蒙汉人民历久相传,共同喜爱。 纵观达拉特文化发展史,蒙古族以博大胸怀不断吸纳外来文化,使达拉特文化形成以蒙汉文化融合为主流,以蒙、汉、藏文化相互交融为特色的典型地区文化。而达拉特文化之中,在有形的实体文化之外,长期历史上凝聚形成的最可宝贵的是鲜明的地区文化传统。由于鄂尔多斯部在漠北长期守护“大禁地”,达尔扈特又世代专奉祭礼,生活在达拉特的蒙古人对成吉思汗拥有至高无上的虔诚崇拜与英雄信仰,成吉思汗时代形成的蒙古族勇往直前、果敢英武的民族精神,在达拉特蒙古族人民中间世代传承。藏传佛教以“六道轮回”为主旨的麻痹教化并没有使蒙古人从根本上放弃这种勇于进取的民族精神,汉文化输入、农耕开发加快使很大一部分蒙古族群众在身为奴隶的同时又沦为汉族地商的苦力,从而使蒙汉群众在阶级利益上结为一体不断爆发反抗,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现实促使蒙汉人民共同凝聚在蒙古族民族精神的旗帜之下,反抗压迫,奋起斗争,达旗近、现代史上杀洋灭教、“独贵龙”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使蒙汉人民的团结更紧密,敢于拼夺,勇往直前的精神凝聚力不断增强、不断发扬光大,而这种既存在于达旗历史文化之中,也存在于达旗现实文化之中的地区民族精神,是以蒙古族传统的民族精神为核心而形成的。达旗的地区民族精神,对民众心理思维和行为习惯影响甚深,是达拉特地区本体文化中宝贵的财富。 遗存的厚重性 达拉特境内的文化遗存,是达拉特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遗存载托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黄河古渡 黄河为达拉特造就了广阔的冲积平原,同时也对达拉特形成漫长的封锁线,历史上的黄河渡口便是达拉特人与外界联系和走出封闭的重要通道。黄河奔腾万里,渡口繁若星辰,兴废更替,不计其数,然而大河上下堪称“古渡”的渡口并不多。今天达拉特沿河的许多渡口,如贾家河头渡口、田家圪旦渡口、九小渡口等,都是现代河运的产物,明、清时的南海子渡口、萨拉齐渡口已基本废弃。然而,我们确实拥有真正的黄河古渡——昭君坟渡口。昭君坟渡口开创于何时现已难以考证,最早见于史书记载是在汉代,时称金津渡。黄河上的这个古渡,对于达拉特来说,承载过漫长岁月的风雨洗礼,积淀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秦直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听信“亡秦者胡”的谶语,派大将蒙恬率兵北击匈奴至高阙(今巴盟临河西北石兰计山口),并于公元前年至年用两年半时间修筑了一条直道,南起咸阳附近甘泉山,北至达旗境内昭君坟渡口,使秦皇的骑兵三天三夜即可由咸阳驰抵阴山脚下。“秦直道”从陕北进入鄂尔多斯后南北纵贯达旗全境,经历两千余年风雨洗礼,跨越古往今来世事沧桑,达旗境内“秦直道”遗迹清晰可见,青达门乡朝报沟村附近,存一段黄尘古道,竖几座豁口山岗,人工开凿之山口遥遥相对,绵延十数里大道如廊。“秦直道”虽然是古代国防公路,对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天的包西公路、包神铁路在达旗境内与古代直道平行伸展,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跨时代对接启示我们: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合,达拉特这块土地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和神奇的造化,从古至今大路通天。 昭君坟 作为“胡地”的达拉特,在漫长历史上曾经是匈奴的乐园。公元前33年王昭君作为“胡汉和亲”的使者来到塞北后,可能在达旗沿河地区有过较长时期活动。达旗境内白土梁出产的白粉球,民间传说为昭君的梳妆袋生化而成,这经久不衰的传说是达旗人民怀念王昭君的口碑史料,达旗境内的昭君坟虽然未必真是昭君坟冢,但无疑是昭君长期活动铸成的丰碑,是达旗人民纪念昭君功德的事实上的象征物。“胡汉和亲”也确实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承载过的历史文明。 王爱召与“八白室” 王爱召建成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年),到折被毁,共历年。王爱召是蒙古族引进藏传佛教后在蒙古地区建立的最大召庙,成为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文化中心,时有“东藏”之称。清朝实行盟旗制度时,将鄂尔多斯七旗扎萨克的会盟地点定于王爱召,并按“大庙”的意思,将鄂尔多斯定名为“伊克昭盟”。 王爱召建成后,设专殿供奉蒙古族中兴之主达延汗及鄂尔多斯历代领主,鄂尔多斯部将象征成吉思汗陵寝的“八白室”也供奉于王爱召。后来,额璘臣任伊克昭盟盟长期间将“八白室”迁往其封地郡王旗。由于“八白室”曾长期供奉于达旗的原因,以祭成陵为代表的蒙古族祭祀文化在达旗积淀很深。 “会盟”曾经为王爱召营造出高歌美酒的氛围,更给达旗历史打上了特殊的烙印,清王朝通过盟旗制度对蒙古族实行残酷的阶段压迫与民族压迫,在“会盟”时体现的更明显更集中。 《蒙古黄金史》与罗卜藏丹津 中国历史文库中有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黄金史纲》,亦称《蒙古黄金史》,与《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共称为有关蒙古史的三大历史著作。《蒙古黄金史》的作者为达拉特旗阿什泉林召著名喇嘛罗卜藏丹津。《蒙古黄金史》约31万字,对蒙古兴起前后的历史记述较详。美国、苏联、日本、西德、比利时、蒙古等国都曾翻译出版。 罗卜藏丹津精通蒙、藏两种文字,曾编著《蒙藏辟典》,于清朝康熙年间建阿什泉林召朝克庆独瓜。因主持佛事有功,清庭曾下诏允其建“御诏普化寺”。罗卜藏丹津出生于年,卒于年,圆寂之后其佘利子葬于阿什泉林召后面的宝塔。 历史悠久,文化典型,遗存厚重,构成达拉特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基本特色,勇于创新,勤于劳作,敢于进取是达拉特旗蒙汉各族人民世代承继的文化传统。发掘和继承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以与时俱进的理念对地区本土文化扬善弃劣,努力发扬光大群众共同体长期形成的优秀品格和精神,摒弃地区文化形成过程中必然伴生积淀的自负、排外与保守,为建设富庶、文明的达拉特而努力奋斗,让达旗地区文化以鲜明的时代风采焕发新的生命活力,是达拉特人的时代使命。 载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达拉特报》 亲和有识之士 倾诉血脉深情 剖析社会万象 解读历史人文 弘扬辩证思想 维护正义公平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ongxinge.com/zxls/1482.html
- 上一篇文章: 中国历史上首个出现以中兴二字命名的时
- 下一篇文章: 就在刚刚15点51分,中国股市宣布两大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