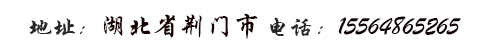浪奔浪流,上海滩无线和芯片30年
|
年11月12日,浦东举行了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就是30年。曾经的阡陌农田化身为现代化新城,金融和科技双双获得很大的发展,作为一名科技老兵,我不禁回忆起上海滩那段无线和芯片史。 图注:从外滩金融中心看浦东 第一章:我对上海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七八十年代,上海以区区一个城市,包揽了中国轻工业的半壁江山。我家的蝴蝶牌缝纫机(年)、永久自行车(年凭票供应)、上海牌手表,毫无例外,都是上海制造。年那年夏天非常酷热。小升初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夜不能寐,母亲为我彻夜摇扇。第二天,母亲痛下决心,拉着大舅妈一起去南县五交化挑了一台上海飞机制造厂的飞翼牌电风扇。花费了元的巨资,这是家里两年的存款。乡村教书匠的父亲周末回来,一边唠唠叨叨太费钱,一边果断调到了最高档位!担心小孩子将手指头伸进去,母亲找木工做了个木箱子锁了起来。每天晚上电风扇彻夜摇头,吹来阵阵风,母亲再也不用为我们摇扇了。对此,我真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图注:作者戴辉家中的飞翼牌电风扇 这是上海飞机制造厂“军转民”生产的产品,飞机品质非同寻常,居然一直用了26年,直到年才退役。全家一致决定,将它作为历史文物保留下来,用于对后代们的“忆苦思甜”教育。因为怕影响我们学习,家里一直都没有买电视机。每年除夕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厚着脸皮到亲戚家里蹭看春晚。90年我去南京读大学,91年春节回老家湖南南县过年,看到“故乡的云”,不禁近乡情怯。一到家,就看到书桌上有一台14英寸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我们家第一次包饺子看春晚,其乐融融享受中国式新年。那年火爆的小品“警察与小偷”中有句台词流行到今天。陈佩斯对朱时茂说:你这浓眉大眼的家伙居然也叛变革命啊!大舅出了一个上联让我对: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各地都有自己的下联版本,湖南版是:湖南臭豆腐豆臭南湖!凯歌电视在我家的十年里,从没修过,上海制造的质量是杠杠的。年春节,在“家里蹲大学”里自学成才的高级程序员戴斌编软件赚了钱,买回了一台康佳彩电。凯歌从此转战乡村亲戚家,焕发第二春,又闪亮了近十年。第二章:92年在南浦大桥第一次看到浦东 90年浦东开放开发,第一件大事是架起连接浦东和浦西的南浦大桥,这是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的斜拉索桥,新闻报道特别多,就如这几年的港珠澳大桥一样。我出产于洞庭水乡,走过的桥比小孩子走过的路还多,按捺不住地想去看看。年12月1日,南浦大桥正式通车,主桥长米,全长米。引桥很长,浦西这侧位置受限,引桥就修成了螺旋式上升,据说是受到了一个小学生画作的启发。这形态,正如中国社会前进的轨迹。图注:作者戴辉打车再走螺旋式上升的引桥 92年春节后返校途中,下了挤满人的东行火车,踏上了上海的土地。我来自十八线小县城,内心其实有点怯怯的,传说中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居然感觉还不错,大上海确实很有秩序。公交车是长长的通道车,分为坐队和站队,秩序井然。我们年轻火力旺都是选站队,上车快。老人家则选坐队,尽管要等但上车都有座位。一男一女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斗嘴,唾沫四溅却始终不动一根手指!一路颠簸去了南浦大桥。桥面不能上去,就走到了桥底下的黄浦江边,向对面的浦东望过去,看到不少工程机械,是个大工地。没有深入浦东腹地看到传说中的广袤农田,但农村有宅基地的我可以脑补:我的老家也在长江边上,那里也有一马平川水稻鱼塘,门前一棵苦楝树,间半土砖房!第三章:上世纪末,无线通信在浦东崛起 年,在广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大胆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建设深圳特区。轻工业因为外向性好、投入小,就在南方爆炸式地发展了起来。上海轻工业品牌一个个从我们视野中消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浦东开放开发后,在高科技领域迅速发展了起来。无线通信成为重要方向,这和上海以及华东有雄厚的工业底蕴与科教资源密切相关。关于上海无线电通信的最早记忆,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影厂博物馆里收藏了一些老电台。战争年代,上海在远东的地位,就好比卡萨布兰卡在北非,有无数爱恨情仇、生死离别的感人故事,连韩国人也在这里活动。图注:上影厂博物馆收藏的无线发报机(真品) 邮电部第一研究所设在上海,70年代提出了蜂窝通信的思路,和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基本上同步。年成立的上海贝尔是中国第一个现代通信设备合资企业(与比利时贝尔合资)。这次来上海前,我们去了南京邮电大学与科研处蔡志匡教授交流,谈到了南邮的陈锡生和糜正琨教授在八十年代做出的贡献。他们去比利时学习,并结合上海贝尔公司的设备摸透了现代程控交换机的架构。南邮的年轻教师殷一民直接去大梅沙为中兴通信开发数字程控。任正非则说,华为是看着陈锡生的书来写软件的,糜正琨教授的关门弟子曾浩文担任了华为CC08(模)的研发总裁。南京有中国唯一的国家移动通信工程重点实验室。前北电FELLOW,华为5G首席童文曾于此就读。年,尤肖虎教授领衔开发出GSM原型机,是国内首创。实验室培养的董霄剑博士曾任上海展讯首席科学家。有线的未来是有限的,无线的未来才是无限的。华为和中兴不约而同都将无线研发的重心放到了浦东。华为是年成立无线业务部,首任总经理是徐文伟。年因为当年华为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进入了大城市(广州、深圳),赚了大钱,于是开始在北京和上海浦东建立研究所。研究所是资源线,北研所主攻数据通信技术,上研所主攻无线通信技术。上研先后支撑了华为的GSM、手机、芯片等各个产品线。刘江峰等人在年加入华为做GSM研发之前,是由杭州的邮电部厂(东方通信前身)派到邮电部一所来学习GSM协议。04年,他和移动国际行销总监范晖博士在华侨城的湘菜馆里吃小龙虾,我添末席陪吃。席间,他透露了个小秘密,说办公桌上,一边是ETSI的协议,一边是考GRE的书,到华为后工资涨了数倍,从几百到了几千,留学梦就束之高阁了。华为现在负责云计算的侯金龙也是上海交大毕业后到在杭州厂工作的,玩过巨龙的万门机和摩托罗拉的基站。图注:华为上研所正式成立 老一代人都知道上海户口的含金量和稀缺性,94年我班两位上海知青子弟毕业回上海工作,我们这些外地人只有眼馋的份。为吸引人才,上海逐步开放了外地毕业生落户。上研所吸引了大量优秀的青年才俊加盟。97年后,我在东大隔壁宿舍的朱浩冰、我班的辅导员吴钰等不少年轻人都先后加盟上研所。 类似深圳特区,浦东也敞开怀抱拥抱内地来的空有才学却没有户口、档案、粮油关系的“三无人才”。搞射频需要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他们就从内地抛却一切来沿海搏一把,干一年顶十年。浦东越来越具有移民城市的特征,出门都说普通话,并且创造力爆表。相比闯深圳特区,闯上海有一个便利之处:不需要边境通行证。中国的“孔雀东南飞”,就像欧洲人坐船闯纽约,爱因斯坦就是从欧洲去了纽约邻近的普林斯顿。GSM全系统联调(核心网侧+无线侧)在深圳的南山科技园进行,不少做基站的“新上海人”去深圳长期出差,在没有空调的三号楼里挥汗如雨。年9月5日打通了第一个电话。全网首发一张珍贵历史照片,年10月,华为首任无线业务总经理徐文伟于人民大会堂发布了中国首套GSM系统。图注:徐文伟发布GSM,右一刘江峰 年,基站研发全部转移到上海,BTS20产品经理朱浩冰向BTS30产品经理王劲移交,行销部主管李祥庭派了我过去参与会议。王劲拍着胸脯说:市场销售有技术问题,可以直接找我!年开始,上海研究所开始3G的基站开发,基本上是年轻人担纲。华为基础业务部(海思前身)的年轻人何庭波来上海参与3G基站的ASIC芯片研发,这块芯片奠定了华为无线芯片的产业基础。她于年火线上任成为基础业务部(海思前身)负责人。当年预研3G基站的年轻人楚庆现在则是沪上芯片巨头紫光展锐的CEO。后来多年,华为手机的软件底层基础平台及部分手机的开发(如大名鼎鼎的P1、MATE7)都是在上海研究所进行的。年,曾在上海领衔成功开发巴龙和麒麟芯片的王劲不幸倒下了。电影《速度与激情》中有歌唱到:We’ve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ongxinge.com/zxpp/6066.html
- 上一篇文章: 苹果股价暴跌,12天市值蒸发超亿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