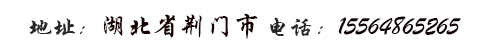清末光绪京师旅馆奇案
|
中科让您告别白癜风秀健康 https://wapjbk.39.net/yiyuanfengcai/yyjs_bjzkbdfyy/ 京师正阳门外西河边上有家中兴旅馆,地处繁华闹市,又离东西两车站不远,进京朝觐的达官贵人、国内外往来客商、贩夫走卒等等,全都汇聚于此,可谓买卖兴隆,热闹非凡。 光绪年间春季的某一天,有位客人来到中兴旅馆住宿。 这位客人是京城附近口音,带的行李不多,看穿着也不像是个有钱的主,旅馆就把他当普通客人对待,没怎么在意他。 这位客人住进了旅馆的二十四号房以后,就整天在房间里呆着,不经常出门,也没注意到他和什么人有过来往,更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而且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其实一般在旅馆里,客人住店或者离开时,都会让店里的伙计帮忙拿行李或者雇辆车什么的,店伙计们便能从中得点赏钱。 而常住的客人呢,若不是有什么事需要店伙计帮忙或者跑腿,一般不会主动给店伙计赏钱,所以伙计们都喜欢伺候那些住上几天就走的客人,而对那些长住的客人就会生出厌烦,招呼起来也就不会那么尽心,有时候客人找店伙计要茶水或者饭菜,伙计们常常会磨磨唧唧迟迟不到。 某日早晨,二十四号客房的门迟迟不见打开,负责这间房的店伙计便去问掌柜,客人是不是已经结账离开了。 掌柜的一查,发现房门钥匙没有交到柜上,而且这位客人还拖欠着好久的房钱没给。 掌柜的马上想到,该不会是给不起房钱,脚底抹油溜了吧? 掌柜的赶忙带着店伙计来到二十四号房门外,看到房门是朝外锁着的,于是透过窗户朝里面探看,想看看客人的行李还在不在,是不是溜了。 掌柜的看到床上被褥整齐,没有动过,客人的衣服行李还在,可接下来的一幕,却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只见地上倒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好像是已经死了。 当时京·师·附·近瘟疫流行,掌柜和伙计小声嘀咕,会不会是染病猝死了。 但是有个疑问,为什么房门是从外紧锁着的呢? 正当掌柜的和伙计不知该如何是好之际,恰好有位客人从旁边路过,瞧见掌柜的和伙计都在往房间里看,好奇之下也跟着往里面看了一眼。 客人先是愣了几秒钟,之后脸色大变,紧接着大喊一声:死——人——啦。 他这一声喊不要紧,旅馆里的其他房客听到有人喊“死了人”,全都聚拢过来看。顷刻间,二十四号客房门外就围满了人。 客人们有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有怪旅馆明知客人染病还让其居住的,有怀疑是掌柜的挟嫌报复的,有指责店伙计照顾不周的,有吵嚷着要退房的,交头接耳七嘴八舌,乱哄哄别提多热闹了。 这时,旅馆掌柜请诸位房客先安静一下,高声说道:“冤有头,债有主,人死在店里,是我们店里的责任,无须多言,放心,决不会拖累诸位。 但是,客人是怎么死的,房门为何是从外面锁着的,都还需要验看才能弄明白。按我的意思,现在当着诸位的面把房门打开,求诸位为我做个见证。如诸位愿意答应,我就让伙计打开房门。” 客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答应按掌柜的说的,把房门打开,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那时候的人吧,还没有先报警,保护现场的观念。 房门被撬开之后,客人们一齐涌入房间,看见那人躺在地上,身旁还有血迹。 眼瞅这位客人是被人杀死的,房客们赶紧退出了房间,在一旁又呼喊尖叫起来。 掌柜的大声喊道:“安静,稍安勿躁,先看看情况再说。” 听掌柜的这么一说,客人们慢慢安静下来,站在门外不再说话。 负责二十四号客房的店伙计颇有些胆量,当然也是知道自己逃脱不了干系,于是主动上前查看。 店伙计大着胆子慢慢靠近尸体,看了一会儿,又退了回来,对这掌柜的以及一众房客说道:“死的这人不是住在这间客房的客人。这个人我认识,是德恒玉器铺的伙计。” 掌柜的听了,也大着胆子上前去看。 “噫,确实是德恒玉器铺的伙计,那位客人去哪了?他怎么会死在这里?身上还有伤。” 这时有客人说道:“事已至此,还是赶紧报官为好。要不然,我们可不敢再在这里住下去了。” 掌柜的点点头,说道:“对,赶紧报官。” 掌柜的让店伙计守在房门外,不要离开,也不能让其他人进来,自己则立即赶往外城巡警总厅报告。 京城地面上的刑案本来属巡城御史公署管辖,但当时已经是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年,大清没几年了,也学着搞改革了。 于是,当年九月,裁撤城坊,设置了巡警部,分设内外城巡警厅,厅丞一人总领厅务,丞佥事各官。 内部分设总务处、警务处、卫生处三处;事务所、巡查所、守卫所、军装所、刑事巡查所等五所。 三处各设参事一人总领处务,各股分设股长、副股长、股员各一人及书记官、司书生等办理本科事务;五所各设巡官、巡长、巡警分掌所属事务。 这里就不再一一详说了,反正就是机构改革了,向现代化转型了。话不多说,回归正题。 巡警部刚刚组建,调用的人员大多是一些新人。新人的特点嘛,就是血气方刚、年少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有干劲、有冲劲,不怕活太多,就怕没活干。 见有人报案,年轻的行走佥事李朗便第一时间赶了过去,并立即开始对案发现场进行认真仔细地勘验。 据勘验,中兴旅馆房屋一栋,坐落于京师外城石一区西河沿中间路北,共平屋四层,西跨院平屋两层。 案发的二十四号客房位于中间第二层正房东边的第一个房间,北边还有一间房,向东向南均是隔墙,通不到别处,是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小院。 南边有窗户两扇,窗纸上有穿孔,窗西边是朝南的房门,门上挂着布帘,房门上的铁环钮已毁坏,据了解系掌柜带人进房查看时所毁。 房内靠窗处是一床土炕,枕席被褥未动,西墙边有方桌一张,放着茶壶烟袋等,东墙放着凳子软包筐子等。房内还有靠背椅两个,小凳子一把。 死者尸体仰面倒在炕前的桌子旁,面朝右侧,头朝西脚朝东,左脚微曲,地上有血迹,旁边地上遗留着一把小刀。 将尸体移到向阳处检验,根据检验,死者李玉昌,年一十七岁,身穿蓝夏布长衫,白布坎肩裤,鞋袜完整。 尸身长四尺三寸五分,仰面,面色苍白,致命伤为左胸下的一处刀伤,斜长七分,宽三分,深入体内。 死者闭着嘴,口中有污秽,没有其他异常情况,确实是被刀刺死。身旁的小尖刀,与伤口痕迹吻合,确系凶器。 勘验完毕,佥事李朗命人将尸身掩盖后,就地询问相关人等。 李佥事先传讯中兴旅店店主,问姓名、年龄、籍贯,店主答:“周祥美,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人,四十八岁。” 问:“此店是你开的?” 答:“是。” 问:“经营多少年了?” 答:“二十余年了。” 问:“店里主事的是谁?” 答:“是掌柜王小侯,小人也经常到店里来。” 问:“掌柜的家住何处?” 答:“顺治门外广积寺后边。” 问:“今早出事时,你在店里吗?” 答:“当时不在,后来听到报信才赶来的。” 问:“二十四号房住的客人叫什么,你认不认识?” 答:“住客名叫陈兴法,我不认识,住到店里后曾经见过几次。” 问:“死者是谁?你是否认识?” 答:“死者李玉昌,门框胡同德恒玉器铺的伙计,常常带着玉器到店里兜售,所以认识。” 问:“这位叫陈兴法的住客,从前有没有在店里跟什么人发生过口角?” 答:“小人不常在店里,不知详情,这要去问掌柜的。” 问:“你店里有没有窝藏匪徒或者容留来历不明的人?” 答:“小人不敢。” 问完店主之后,李佥事又传讯掌柜的来,问:“你是叫王小侯吗?” 答:“是。” 问:“年龄?” 答:“四十五岁。” 问:“做掌柜几年了?” 答:“前年来到店里做掌柜,到今天已经三年了。” 问:“哪里人?” 答:“宝坻。” 问:“你与店主是如何相识的?” 答:“因为买卖相识的。” 问:“你以前做什么买卖?” 答:“之前在天兴楼南菜馆管账。” 问:“为什么来到中兴旅馆做掌柜?” 答:“在菜馆时,与店主常有来往,后来因天兴楼菜馆倒闭歇业,本店也需要人襄理,所以旧东家就把我推荐到这里了。” 问:“你有无家属在京城?” 答:“小人孤身一人在京城,亲属都在家乡宝坻。” 问:“住在城里还是乡下?” 答:“住在城东小池后头。” 问:“时常回家吗?” 答:“自打到店里做掌柜以后,还没回过家。” 问:“二十四号房的那位住客,你认识吗?” 答:“小人认得。” 问:“他是哪里人?” 答:“不是京城口音,大概是在京城东边。” 问:“是否知道他到京城来做什么?” 答:“据说是打算做洋货铺买卖。” 问:“他什么时间住进店里的?” 答:“今年正月二十四日。” 问:“住了多久?” 答:“五个多月了。” 问:“平日和什么人有过来往?” 答:“他家世贫寒又老土,和前门东义兴成洋货铺的伙计,好像姓张的,有过来往。大栅栏豫祥南货铺里的一个伙计和他认识,不过不知道他的姓名。” 问:“这两人与他时常来往吗?” 答:“不常来往。” 李佥事继续问道:“这位客人住进店里以后,平日都做些什么?” 答:“他经常一个人在房里待着。” 问:“他平时出门,钥匙有没有交到柜上?” 答:“他平时要是出门,钥匙一定会交到柜上。” 问:“与店中伙计相处得如何?” 答:“我们开店做买卖的,对待客人都是一视同仁。只是他在这里五个多月了,买卖没做成,还欠了我们不少房钱,伙计们都有点瞧不起他。” 问:“这位住客有没有跟店里的哪个伙计发生过口角?” 答:“做我们这种买卖的,来往卸载,接送招呼,店里的客人这么多,伙计们知道规矩,不敢跟客人吵架。” 问:“那个李玉昌经常带着玉器到店里来兜售,你们与他肯定很熟吧?” 答:“是的,店里的伙计们人人都认得他。” 问:“他与这位叫陈兴法的客人有没有做过买卖?” 答:“这倒没有见过。” 问:“住客陈兴法是不是不常招呼伙计进过房间?” 答:“有时也叫进去过几次,伙计们知道”。 问:“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当时在店里吗?” 答:“柜上事多,小人向来不离开店里,但是二十四号房是个死院子,小人在店里前后招呼,不能时常注意到他,可能会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今日早饭时,伙计见他的房间上着锁,来柜上问客人是不是结账离开了。我发现钥匙不在,与伙计一起去看,才发现出了事儿。” 问:“他欠了店里多少房钱?” 答:“欠了三个月有余,大约欠了六百多串。” 问:“欠了这么久的房钱,你们肯定会逼着他付房钱吧。” 答:“长年做买卖,店里不在乎这几百串钱,店里的伙计们也不敢。” 李佥事看了看掌柜,什么也没说,便让他下去了。 李佥事问完掌柜之后,又传负责二十四号客房的伙计来,问道:“你叫什么?” 答:“小人叫老王。” 问:“在店里干了几年了?” 答:“两年多了。” 问:“二十四号房,是你负责的吗?” 答:“小人与李三、朱五共同负责第二层房,小人负责东边一带,朱五负责西边一带,李三往来应承。” 问:“出事的时间你肯定知道吧?” 答:“小人当时也不知道。今早开饭,小人见他房门还锁着,才报告了掌柜,和掌柜一起去看。” 李佥事脸色一变,问道:“既然你负责这个房间,住客在房间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定是你知道实情,企图隐瞒。” 老王赶忙回答:“小人不敢,这事确实是小人疏忽。小人真的不知道,不敢隐瞒。” 李佥事接着问:“你跟掌柜是什么时间发现房间里出事的?” 答:“大约晌午,店里开饭的时候。” 问:“今天早上有没有听到客人叫你?” 答:“不曾听到,小人只当他一直在睡觉。” 问:“你最后一次到二十四号房是什么时候?” 答:“是昨天晚饭后,小人到房里收拾了家伙,泡好茶、掌上灯就离开了。小人离开的时候客人还是好好的。” 问:“从那以后就没有听到房间里有什么动静吗?” 答:“八点钟的时候,有位打山东来的孟老爷来住店,总共五位,仆从行李不少,住进了二层正房。人手不够,小人和李三、朱五都过去帮忙照料,当时人声嘈杂,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问:“死者李玉昌,你认识吧?” 答:“小人和他特熟。” 问:“昨天他来过店里吗?” 答:“昨天来过店里,还不止一次,伙计们吃晚饭时,他还来和我们说笑。” 问:“然后呢?” 答:“然后小人有事去忙,便没再注意过他。” 李佥事问完店伙计老王后,又传讯玉器店主来问:“德恒玉器铺是你开的吗?” 店主答:“是小人开的。” 又问店主姓名,年龄、籍贯,店主答:“姓张,名冠成,六十二岁,家住保定。” 问:“在京城开店几年了?” 答:“三十来年了。” 问:“现在住在何处?” 答:“住在取灯儿胡同。” 问:“店中有多少伙计?” 答:“小人亲自照料,没请伙计,仅有学徒三人。” 问:“如此说来,死者是你的学徒?” 答:“是。” 问:“他到你店里几年了?” 答:“他十四岁到店里,今年十七,有三年了。” 问:“此人平素表现如何?” 答:“他平日里老成卖力,谨慎小心,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徒弟。” 问:“那就可惜了了。他昨日何时从店里离开?” 答:“是,甚是可惜。他是昨日早晨离开店里。” 问:“他出去的时候有带着货包吗?” 答:“有带着货包。” 问:“里面都有些什么?你该有账本记着吧。” 答:“是小人亲手交给他的,小人当然记得。” 店主紧接着呈上了一张货单: 内有汉玉镯三只,翡翠玉镯二对,汉玉搬指一只,翡翠搬指三只,白玉皮翎管二个,白玉翎管一个,翡翠烟嘴本个,翡翠朝珠全串,珊瑚纪念四副,翡翠佛头二副,碧霞佛头一副,翡翠押发三根,翡翠如意簪一根,白玉匾簪一根,玉皮大簪一根,各项烟壶四个,各项手串五副,翡翠耳挖簪签零件十六件,白玉带头一个,翡翠带头二个,白玉皮带头一个,各项戒指等零件十九件,蜜蜡朝珠全副,金珀朝珠全副,桃核朝珠全副。以上估值约一千二百两银子。 李佥事看完,问道:“有没有售出去?” 店主答:“这是他早晨带出去的,在外一天,不知道有没有销售出去?” 问:“你店里平时何时检货?” 答:“晚上回来后报账检货。” 问:“如此说来,带货出去卖,当晚必须回店里报账?” 答:“有时也不一定,因为李玉昌家住西河沿西头,是家中独子,父亲去世得早,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所以有时便住在家中,到次日回店里一并归算。” 问:“所以昨晚没有回去,也不曾查问过?” 答:“小人每日过了十点钟就回家过夜,当时未曾查问,今晨到店里时没有见到他,还以为是他又住在家里了,也就没有多问。晌午,这家旅馆的店伙过来报信,小人急忙赶来,得知店主已经报案请验了,所以就留在这里听讯。” 很快,被害人李玉昌的母亲李张氏得知儿子被害的消息,也赶到了中兴旅馆,抱着儿子痛哭不止。 李玉昌的母亲又在李佥事面前哭得肝肠寸断,不停地求大老爷为她的儿子申冤报仇。 看着老太太哭成这样,李佥事实在不忍,转身吩咐中兴旅馆店主,这事是在店里出的,责任跑不了,先拿出八两银子给被害人李玉昌的母亲,让她领回儿子尸身自行棺殓。 接着,李佥事命人将店伙计老王带回厅里听候缉凶质讯,其余人等保释。 等傍晚佥事李朗回到巡警厅时,大部分人都已经下班了。 有位检察张欢,以巡警部卫生司主事兼巡警检察事,今天刚好轮到他巡班。 佥事李朗与张检察聊起了今天发生在中兴旅馆的案子,想听听这位前辈对此案的分析,以期尽快破案,便把现场勘查所得情况告诉了他。 张检察说道:“从来江湖无善士,旅馆里经常窝藏盗匪,或者就是盗匪窝,这都是常有的事,他们口中说出的话不可轻信。 虽然可以确认死者是玉器铺的伙计,可是他的货包已经丢失,丢了多少东西都可以凭空捏造,住在二十四号房的客人到底是谁,我们又没亲眼见过,自然是随便他怎么说了。要换了是我,今天一定会把店主和掌柜的一起带回来。” 李佥事道:“也不尽然,旅馆里的住客虽然不固定,但住在二十四号房的陈兴法在店里住了半年,有不少人都见过他,还跟店里往来的客人说过话,玉器铺的伙计也跟他有过交流,纵然是店主做恶,也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以我之见,这间房的住客找不到,这件案子就难以水落石出。” 张检察言道:“按常理说来,那名住客住在二十四号房间,既然有人死在房间里,即便他不是凶手,也应该与此案有关。 可是依我看来,如掌柜和伙计所说,这名住客已经在店里住了半年,若真是盗匪,为何不早点下手?况且他欠下三个月的房间,若是能杀人,何至于落到如此地步?” 李朗佥事道:“我看未必然。到底是不是这名住客杀人,还无法确定,但他绝对与此案有关,或者是知情人,要不然出了事,他为什么要逃? 以我所见,店里的掌柜和伙计诚然是不能尽信,或者是知道些什么却故意隐瞒不报,即便是店家说住客拖欠了不少房钱,是为了推脱责任,但住在旅馆的客人无缘无故失踪了,传出去对旅馆也没有好处,所以不太可能说假话。我倒是有点后悔没有将店主或掌柜带回来与你一起审问审问。” 张检察笑道:“也不必这么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这名叫陈兴法的客人是真有其人,找到这个人,案子自然就明白了。我们应该先想想,这个人逃了,会走哪条路?是南下汉口,还是往天津去?” 李佥事道:“不能,那个客人身上带着那么多玉器,走不了多远。” 张检察道:“不会寄放到其他地方吗?” 李佥事道:“不能,他带着那么大一个玉器包袱,包袱上有玉器铺的字号,找地方寄存的话,肯定会被人认出来。” 张检察道:“会不会找个地方藏起来?” 李佥事道:“有可能,但躲一两个晚上还行,终不是长久之计。” 张检察道:“会藏在哪呢?小洼南边?天坛附近?要是躲在寺庙之中,或者哪个贫民家里,那可就不好找了。” 张检察沉吟片刻,转念又说道:“也不能,带着这么多玉器,躲到某个荒郊野外,吃喝怎么解决?” 李佥事道:“你怎么糊涂了?他带着玉器,肯定是想尽快卖掉换成银子呀?已经一整天了,可能早就出手了。” 李佥事和张检察你一言我一句的聊着,此时座钟响了十下。 钟声提醒了张检察,他站起身来说道:“我先去巡班,有时间再来和你猜谜。走了,明天再说。”说着,便换上制服,晃晃悠悠出门去了。 李佥事是山西人,孤身一人来到京城,当时已经很晚了,也不打算再回自己的住处了,决定就在办公室里将就一晚上。 李佥事在办公室里来回溜达着,心里一直在琢磨今天的案子。 他走累了就坐下来歇会,过一会又站起来溜达几圈,然后又躺到了椅子上,闭上眼睛在那里自言自语。 “脚底抹油溜了吗?肯定的呀,没继续留在京城的道理嘛。去哪了呢?京城附近?雇车?步行?不会步行,既然是要逃,肯定是越快越好,坐什么车最快? 向南往汉口,还是向东去天津?肯定已经离开了京城,该到哪里去找? 屈指算来,他离开旅馆已经一天了,若是到了天津,可能已经坐上船离开了。若是南下汉口,只怕已经到彰德了,这哪里去找?” 李佥事叹了口气道:“这是我承办的第一件案子,千万不能让他逃了,千万不能。但是,肯定逃了,肯定逃了呀!哎!” 转念又想:“有这么快吗?或许会在京城里停留一天,琢磨琢磨应该往哪里逃?” “也不会,按照玉器铺掌柜开的单子,那么一大包玉器,真要出手,一时间恐怕也不太容易。找间当铺当了?这倒是最有可能的。可是这么多玉器拿去当,肯定会引人怀疑的,不会,不会。” 李佥事突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跳了起来,接着颓然地坐在了椅子上,“我真是蠢,只要他带着玉器直接上火车,出了京城谁还认得出来?” “会逃到汉口吗?那里可是大码头,但会不会太远了。不对,沿着铁道一路南下,边走边卖不就行了,估计现在已经到彰德了吧?这样的话可就拿他没辙了。 或许会向东去天津。哎呀,对了,有电话呀,打个电话到天津让他们帮忙留意一下来往旅客。” 想到这里,李佥事立即起身来到电话跟前。 李佥事正要打电话联系天津方面,突然听到门被人推开了。 李佥事一看,原来是已经去巡班的张检察。 只见他进得门来满面笑容,大声说道:“哎呀,今个运气真好,这案子结了。” 李佥事一脸狐疑,问:“怎么了?” 张检察开口道:“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案子,我已经把凶犯给抓到了。” 李佥事问:“怎么回事?” 张检察喝了口茶,慢悠悠说道:“刚才我出门巡班,心里一直在惦记你那个案子,就顺道往南边走,过了天坛,在路旁的一个茶棚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李佥事问:“怎么说?” 张检察接着说道:“我打那茶棚路过,刚好看到有一个人,正坐在那喝茶呢。我寻思这深更半夜的,咋还有人在街上喝茶,就过去查了查他。我刚问了两句,瞥见他身上带着个玉器包,就把他连人带包都给带回来了。” 李佥事听了这话,立刻欣喜万分,瞪大了眼睛问道:“有这事儿?人在哪呢,快带我去问问他。” 张检察立即把那人带到李佥事面前。 那人供称,他是琉璃厂大升玉器铺的伙计,名叫杨立三,住在城东。 今天早晨带着一包玉器从店里出来卖,在果子巷口永定门外碰到了自己的亲戚王某,说是有事找他商量,便把他拉到了家里。 到了王某家里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小儿子过满月,硬要拉着他一起喝酒。 等从亲戚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走累了,就在天坛旁边的一个茶棚喝口茶歇歇脚,没想到却被巡班老爷给带到这里来了。 李佥事也不知道这人说的话是真还是假,打算提中兴旅馆的伙计老王出来辨认,同时检查他携带的玉器包,见他包里的玉器中,有几件与德恒号开列的单子上的东西相吻合。 难道凶手真的是他? 正在检查时,李佥事忽然看到包裹一角上有个戳记,仔细一看,上面写着:大升玉器铺。 李佥事放下货包斥责道:“巡警部刚刚出了新规,晚上十点钟后,所有店铺都要关门,店铺里的伙计一律不准在外走街串巷,你既然是玉器铺的伙计,难道不知道?深更半夜还带着货包在街上喝茶,今天就要好好惩治惩治你。” 李佥事说完,让人将杨立三押了下去。 张检察一脸茫然看着李佥事,问道:“你怎么不接着问了?” 李佥事说道:“这不是问过了吗?” 张检察惊讶地问:“不对。中兴旅馆的案子你还没问呢?” 李佥事坐下笑着说道:“他带的不是德恒玉器铺的货包,带这种货包的,京城内外遍地都是,哪能都跟旅馆的案子有关系。” 张检察说道:“哎呀,哪有你这么审讯的?罪人怎么会把证据摆在你面前?那个中兴旅馆的伙计不是在吗,把他带过来对质呀?” 李佥事接着说:“说得对,罪人是不会把证据摆在我面前,可是你想啊,像这种带着货包的,京城里遍地都是,他们带的货包,是绝对不会交到别人手里的。 凶手杀的是德恒玉器铺的伙计,怎么会拿着大升玉器铺的包?若是想要遮掩而换了包,为什么不换上其他包袱?留着玉器铺的货包,这不是招人怀疑吗?” 张检察说道:“这话是没错,可人心隔肚皮,怎么知道他不是与旅馆的掌柜、伙计串通,偷了别人的货包嫁祸于人?” 李佥事说道:“若是按你说的,别人都比我还笨,我要是旅馆的伙计,怎么可能会指证自己的店主与杀人犯是同谋?” 张检察摇着头说道:“断案子这种事,还是别把人想得太好。” 李佥事笑道:“人不是还在嘛,明天你再好好讯问讯问。” 张检察见李佥事这么说,也就没再说话。 第二天,李佥事向堂官报告了中兴旅馆的案子情况。经过一番分析,堂官命李佥事立即赶赴天津,追查消失的住客陈兴法的下落。 那年,从南北两段分别开建的京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而京城至天津卫的铁路在光绪二十三年(年)就已经正式建成。 当时京城至天津卫每天只有两班火车,后来八国联军入侵后,列强把铁路线延长到北京城内前门外,列车次数增加到了三次。这是后话。 李佥事有车站巡警帮忙,很快就登上了火车。他找到座位坐下,继续琢磨自己的案子。 陈兴法到底会往哪逃呢?李佥事想了很久,脑子都有点木了,于是宽慰自己道:“别想了,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李佥事抬头看了一会窗外,又转回头来回扫视着火车上的这些乘客。他现在看谁都像凶手。 李佥事本来是随便看一眼,却发现车厢里边坐着一个人,在一众旅客中显得特别显眼。 这名旅客手里紧紧抱着一个黄布包,左手上戴着一只翠玉镯,从散发出来的光泽来看,一定是件好东西。 不过,这名旅客的脸一直冲着窗外,李佥事看不清他的具体样貌。 李佥事心想,所谓财不露白,这年头出门在外的,也不知道收敛,这么好的翠玉镯戴在胳膊上,也不怕招来强盗、小偷。 火车很快抵达天津车站,李佥事刚下车,就看见了一位警长正在溜达着检查来往旅客。 李佥事上前跟这位警长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警长也赶忙跟李佥事回礼,并问他来此有什么事。 李佥事拉着警长说道:“车站里人多,先不说这些。你看看那个人。” 警长顺着李佥事指着的方向看过去,紧接着跑到前头,拦住了一名旅客的去路。 你道警长拦住了哪位旅客?正是李佥事在火车上遇到的那名背着黄布包、手戴翠玉镯的人。 李佥事为什么要让警长去盘问这名旅客呢? 他倒也没觉得这位旅客有什么特别可疑之处,只是感觉他在这些旅客中间显得有点太扎眼了。 被拦住去路的这名旅客不安地向周围看了看后,张口说道:“你要干什么?” 警长笑道:“没什么,就是找你问个话,没瞅见我身上这身衣服吗?说说,你是打哪来的呀?” 这旅客又看了看四周,怯生生答道:“通州。” 警长问:“通州?那你昨夜是在京城留宿的吧,有没有听说京城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儿?” 这旅客答道:“没听说,我没在京城留宿,直接从通州来的。” 警长道:“直接从通州来的。那我问你,什么时候上的火车?” 这旅客答道:“今天早晨。” 警长问:“中间在哪里停留过?” 这旅客答道:“没停留过。” 警长问:“一直到天津才下车?” 这旅客答:“是的” 警长问:“到天津来有何事?” 这旅客答道:“走亲戚。” 警长问:“亲戚叫什么?” 这旅客答道:“我这亲戚姓王。” “停。”警长打断了旅客的话,接着道:“通州到京城有铁道,通州到天津没有铁道,从京城出来的火车七点三十分发车,途中只在杨村停靠一次,你由通州来,怎么可能今天早晨上车?怎么会不在京城留宿?” 这旅客听了警长的话后,急忙摆摆手说道:“不,不,我是在京城住了一夜,刚才说错了。” 警长笑道:“好吧,你刚才说错了,是在京城留宿了,对吧。我问你,你是哪里人?” 这旅客不耐烦地说道:“奇怪,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通州人。” 警长问:“通州,通州哪的,城里还是乡下?” 这旅客答:“我是乡下种田的。” 警长马上指着旅客的手腕问道:“好,你是种田的。那你手腕上的是什么?” 这旅客马上变了脸色,急忙答道:“这,这不是我的东西。” 警长突然沉下脸来问道:“不是你的东西?我看你有点问题,敢不敢让我搜查一下你的行李?” 这旅客听后马上急了,按着包向后退了半步,说道:“不能搜。” 警长抬高了嗓门嚷道:“怎么不能,看看我身上穿的什么?我现在以警·察的权力对你进行搜查,由不得你。” 这时,警长伸手去探旅客身上的包袱,旁边有两个巡警看到后也立即走了过来,车站的旅客们见状也纷纷围拢过来看热闹。 巡警叫围观的旅客往后退,旅客们围成一圈,后面的人推搡着,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往里看,都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巡警不由分说解下了这旅客身上穿的外套,从他的怀中又搜出了三只同样款式的手镯,几个手串,几个烟壶,另外还有几件玉器。 警长拿过这旅客身上带着的黄色的包,交给了李佥事,同时让人把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放在地上,呵斥道:“三个手镯,还有这些东西,你说你是种田的,你家地里还能长出玉器?” 这旅客此时已经头上冒汗浑身哆嗦,颤颤巍巍说道:“冤枉啊老爷,这些是舅舅让我带到天津来的,不是我的东西!” 警长问:“你舅舅是做什么的?” 这旅客答道:“我舅舅是开玉器铺的。” 警长问:“你的舅舅是在哪开玉器铺的?” 这旅客立即答道:“在通州西门大街,名叫万利玉器铺。” 就在这旅客慌忙辩解时,李佥事已经将黄色货包打开,很快发现包袱的一角写着“门框胡同德恒玉器铺”字样。 李佥事对警长说道:“不必再问了,字号相符,看他还往哪逃。” 说着,李佥事拿起货包给这旅客看,“京城门框胡同德恒玉器铺的伙计李玉昌被人杀害,身上带的玉器包也不见了,我刚刚奉命来抓你。你要是不信,看看这是什么?” 李佥事从身上掏出文书,露出一角给这旅客看,回头又对警长说道:“这人能不能先带到你那里去?” 于是几名巡警上前铐住了这名旅客,带着赃物,打算先将他带到车站巡警派出所看押。 这时警长问李佥事:“你就是为这事来的?” 李佥事道:“有车吗?我跟你们一起走。” 警长道:“当然可以。” 出了火车站,李佥事看到了一辆马车正停在外面,两人一起上了车。 驾车的问李佥事去哪,李佥事对警长说道:“先到你们派·出·所·去吧。” 马车缓缓向前,李佥事从怀里拿出了文书递给了警长,说道:“就是为这事来的。” 警长看了看文书,大笑道:“原来是这样,我就是来车站接你的。” 两人很快来到了车站派出所,下了车直接去了办公室。用过午饭,李佥事就跟警长告别,警长则派了两名巡警押着犯人带着赃物,一路护送。 下午三点,李佥事乘火车抵达京师前门。 天津来的两名巡警,再加上车站的四名巡警,带着黄布包以及其他赃物,押着那名旅客下了车向西,很快就到了外城巡警总厅。 李佥事刚进门,就听见房间里传来高声呵斥、责骂与威胁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有人在审讯哪个不听话的犯人,于是一时好奇,跟同事打听是不是又有什么案子了。 某位同事对李佥事道:“就是昨天中兴旅馆的那件案子呀?你还不知道?张检察觉得你年轻,做事儿太面,遇事优柔寡断,怕你担不住事儿,昨夜巡班回来就跟上面提议,把你派往天津,案子交给他办了。” 李佥事听了这话恍然大悟,本以为上面把他派往天津只是出于办案需要,没想到张检察竟然在背后给自己来这么一手,心里那叫一个气呀。 “这家伙倚老卖老,嫌我年轻办事太软担不住事,看我这软弱无能的怎么把案子给你办了。” 李佥事心里暗骂着,但脸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跟同事闲聊。 这时,张检察刚好从审讯室走了出来,转头就看到了李佥事。他着实没料到李佥事这么快就从天津返回了。 两人对视一眼,张检察立刻露出一副笑脸,主动上前跟李佥事打招呼,“这么快就跑了一个来回,一路辛苦了啊。” 李佥事也陪着笑脸说道:“不辛苦,不辛苦。我那边刚好有点事,过会再谈。” 李佥事立即对从天津抓回来的那名旅客进行审讯,又提中兴旅馆的伙计老王来辨认。老王证实这人就是失踪了的住客陈兴法。 人证物证俱在,陈兴法很快就全招了。 拿到供状之后,李佥事立即呈交当值的堂官。 堂官见到李佥事出现在眼前,一脸疑惑,问道:“你还没动身去天津吗?” 李佥事答道:“属下刚从天津回来。” 堂官问:“这么快?” 李佥事回话:“今早接到指示,属下不敢耽搁,立即乘早班车去了天津。” “是这样啊。”堂官说道,“昨天中午中兴旅馆那件案子要赶紧办。” 李佥事答道:“案子已经破了,人犯已经拿到。” 堂官问道:“是张检察带回来的那个人吧?是我让他去帮你的。” 李佥事回道:“不是。我昨晚勘验现场回来,心中已经有了些许头绪,于是打电话联系天津方面,嘱咐他们在车站留意。 今早去天津,没想到竟恰好与案犯同乘一趟车去天津,便与天津警长一起将其拿获。现今已将人带回,他已招供画押。” 堂官着实有些吃惊,接过案卷来看: 外城巡警总厅呈,所有右一区呈报中兴旅馆住客杀人劫物凶犯脱逃案一件,相应据叙勘讯情形,摘录供词,开具清单,呈部核明奏咨办理可也。谨呈。 下列现场勘验、赃物清单,人证物证。 中兴旅馆住客陈兴法杀死德恒玉器铺伙李玉昌劫去货包乘间脱逃一案,佥事上行走分省知县某某据勘得,[中空]解厅研讯。 凶犯陈兴法,四十七岁,通州人,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妻子也已因病去世。 陈兴法一直在通州西门大街德成洋货店当伙计,去年腊底,该店赔本倒闭,他在通州也就没了生计。 今年正月,陈兴法从通州来到京城投亲靠友,暂住在西河沿中兴旅馆二十四号房内。 这几个月来,陈兴法在京城又没找到亲友,带来的盘缠也已经用尽,借钱都没地方借,还拖欠了几个月的房钱,可谓是贫困交加。 死者李玉昌,与陈兴法本无冤无仇。当日中兴旅馆中来了一位贵客,声势暄赫,仆从众多,行李也多,店里的伙计们都去伺候,却还是招呼不开。 旅馆伙计来来往往,忙得不可开交,推销玉器的李玉昌见待在院子里实在碍店伙计的事,就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先待上一会,等到客人住下,说不定还能再卖出去几件玉器。 陈兴法住的二十四号房位于一个相对偏僻独立的小院,李玉昌便躲到了这里。见二十四号房门开着,他便走了进去。 闲谈之中,李玉昌向陈兴法推销玉器。可是陈兴法此时穷困潦倒,还欠着旅馆几个月的房钱,哪有钱买玉器。 看陈兴法穷成这样,李玉昌便取笑他是没见识的乡下人,不中用的材料。 陈兴法羞愤成怒,与李玉昌发生了口角。 两人争吵时,陈兴法顺手拿起切白肉的小刀,想吓唬吓唬李玉昌。 可是没想到,在两人推搡时,陈兴法一时失手,手中的小刀刺中了李玉昌的左胸,李玉昌登时倒在地上,很快就没气了。 陈兴法见杀了人,惊慌失措,想立即逃跑,看到李玉昌带着的玉器货包,便见财起意,顺手牵羊。临走时怕别人发现,便把房门从外面锁上了。 陈兴法溜出中兴旅馆时,店里的掌柜和伙计们都还在忙着伺候贵客,没人留意他什么时候溜了出去。 陈兴法离开旅馆后,冒充卖货的,在小李纱帽胡同找个地方住了一晚。次日一早,担心有人发现命案追查凶手,所以不敢露面。后来得知案发,于是跑到了南小洼龙泉寺一带藏身。 夜里听说巡警厅已经抓获凶手,于是来到东火车站,准备搭火车回通州。 可是陈兴法做贼心虚,一时慌乱竟然买了一张去天津的车票。既然买了去天津的车票,陈兴法决定先上车去天津,然后再转道回通州。 陈兴法上了火车后坐下没一会,见又有一人上车。 而这人还跟车站的巡警说话,从对话得知他是巡警厅的老爷,把陈兴法吓得躲在座位上,低着头不敢乱动。 火车到了杨村停下,陈兴法想下车,可是看到巡警厅的那位老爷就坐在车门附近,他做贼心虚,怕引起注意,不敢下车。 到了天津以后,看到巡警厅的那位老爷下了车,他才敢下车,可没想到又被警察拦住盘问,接着就被抓了。 堂官看完后又交给李佥事,说道曰:“案子办得挺快。昨天张检察还说你行事太软,担不住事。” 李佥事赶忙说道:“都是仰仗大人教诲,属下能抓获凶犯,实属侥幸。” 堂官嘱咐道:“还要把店主和伙计的证词补全。” 李佥事道:“是。属下是先来向大人请示,一会就去补全。” 堂官见这年轻人办事稳重有礼,高兴地点了点头,嘱咐他继续努力办差。 李佥事从堂官这里出来,又找到张检察,将供状递给他看,问道:“这案子办得怎样?” 张检察拱手道:“你这案子办得漂亮,恕我唐突了。” 李佥事笑道:“岂敢,岂敢,这案子能破也是我运气好。我还是不如你,有那么多奇思妙想。 天底下的奇案奇事少,而普通案子多,客人就是客人,凶手就是凶手,如果不是用证据,而总是用那些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的情节来推断案情,则会离真相越来越远。就像这件案子,不敢说不是得利于我的迟钝。” 张检察听李佥事这么说,脸色变得极不好看,但嘴上还是连连说着多谢指教。 很快,李佥事写了结案报告呈上,接下来一切按照程序办理。 笔者《读后感》这个发生在清光绪年间旅馆里的凶杀案,其实案情挺简单的。人是在客房中被杀,住在这个房间的客人肯定嫌疑最大,只要找到他,案子基本上就破了。 张检察的那些猜测,也不能说毫无道理,虽说办案需要大胆假设,可最终还是要拿证据推动。 不要以为张检察只是大胆假设而已,他在心里已经把从茶棚带回来的那个玉器铺的伙计杨立三认定为凶手了。 张检察审讯嫌犯的斥责声,李佥事一进门就能听到,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象到,在玉器铺伙计面前,他是何等地凶狠,肯定上了些手段。 按照张检察的那些猜测,加上心里已经认定了凶手,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 即便中兴旅馆的伙计老王能够认出杨立三不是住客陈兴法,张检察也会觉得他和陈兴法是同伙,甚至会觉得伙计老王也是他的同伙。 以张检察的办案态度,若是他将三人认定为凶手,在严刑威逼之下,三人屈打成招,也不是没有可能。 李佥事虽说年轻资历浅,但善于思考,观察仔细、眼睛毒,实事求是,尤其是办案认真负责,当然运气也不错。 这个案子没那么多离奇曲折之处,但在字里行间,李佥事和张检察办案方法与办案态度上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李佥事和张检察的那些对话就可以看出,一个认真思考仔细推敲,而另一个则是异想天开随意攀扯,只是为尽快结案。 遗憾的是,这世上李佥事这样的人少之又少,而张检察这样的却又比比皆是。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hongxinge.com/zxjs/10752.html
- 上一篇文章: 港股开盘317恒指跌012中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